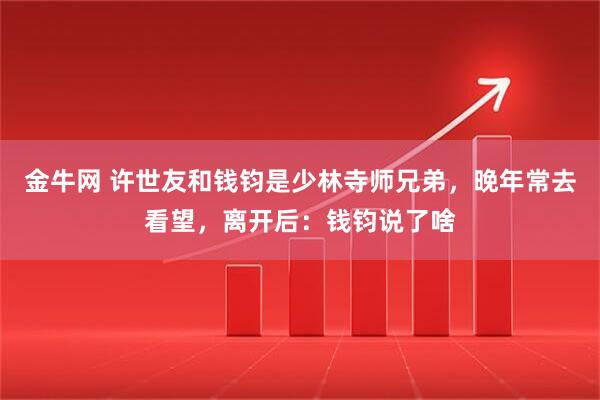
【1984年早春·南京】“老钱,你又躲在屋里喝枸杞水?”许世友推门而入,声音震得木窗嗡嗡作响。钱钧抬头金牛网,咧嘴一笑:“师兄,大嗓门还是没改!”

河南嵩山到南京城,相距千里,二人却像拴在同一根绳上的风筝。相同的1905年出生,相同的贫苦出身,还都在度过少年时代:一个八岁进寺为糊口,一个十三岁逃荒求技。许世友先当杂役,挑水劈柴两年才摸到木桩;钱钧刚进寺就被当家方丈相中,直接触碰少林七十二艺。武路不同,却都靠硬功夫把稚弱身板打成了铁。
奇怪的是,两人在寺里根本没留下彼此的影像。原因很简单——少林俗家弟子近千,白天操练,夜里盘腿念经,谁顾得上聊天。等到1927年前后各自下山,一个北闯,一个南漂,这对师兄弟又一次错肩而过。

真正的“相认”发生在长征途中。那天黄昏,两个人蹲在一截倒木后面啃干粮,许世友听口音觉着耳熟,随口问:“老乡?”钱钧一拍大腿:“开封府兰考!”许世友哈哈大笑:“郑州巩义!咱俩还都挨着。”再捋生辰,再聊练功,才恍然发现彼此是少林同门。枪声在山谷回荡金牛网,二人却为这份巧合乐得像拨开雾的孩子。
之后的战火岁月里,许世友带敢死队砍寨墙,钱钧领突击排端碉堡,两人身上新旧伤疤加起来数不清。许世友曾在鄂豫皖被弹片掀翻,昏迷两昼夜,被抬回时以为牺牲;钱钧也在川北战场被误装进棺材,第二天清晨自己掀盖而起,把守灵的团长吓得连连后退。两个“鬼门关回头客”活成了战友口中的传奇。

建国后路线再次交叠。1955年,许世友进南京主持军区,十年后钱钧被调来任副司令。按理说俩练家子该较量一场,可许世友提过三回都被钱钧笑着挡回去:“刀枪对敌行,对友不使。”许世友撇嘴,仍管钱钧叫“小师弟”,转身却夸“这家伙沉得住气”。

退居二线后,两位老战将都把家安在南京。许世友鲜少应酬金牛网,街巷居民只知道中山陵八号那位胡子硬、脾气猛的老将军。可每月总有那么几天,他会坐吉普车晃到富贵山,掂着一袋茶叶找钱钧。秘书李福海说:“车子刚停,许老就嚷‘快给我倒碗面汤,我渴!’话还没落,钱老在屋里就拍桌子笑。”
两位耳背老人聊天场面颇滑稽:许世友讲起河北平原的骑兵冲锋,声音如锣;钱钧则回忆苏北练民兵,把“朱砂掌”拍碎青石的细节说得神采飞扬。常常是师兄提A事,师弟应B事,听者一头雾水,可他们自己却乐得前仰后合。某次告别回程,秘书忍不住问:“您俩都聊懂了吗?”许世友摆手:“懂啥?见面就行!”

几天后,钱钧也对家人打趣:“师兄走路还虎虎生风,声音比炮弹响,这么硬的家伙,再活二十年不成问题。”说罢哈哈大笑,把茶盅扣得咚咚响。原来,每次许世友前脚刚走,钱钧都会冒一句:“这老头子,心还是热的!”——这便是他“离开后说了啥”的原话,简单,却凝着半生交情。
1985年初冬,许世友病重住院,钱钧拄杖赶去,握着师兄手背低声道:“少林寺那个老槐树还在,我们都在。”许世友眼角湿热,却没说话。翌年许世友去世,军乐声回荡紫金山,钱钧在灵前直立,敬了一个干净的军礼,然后转身离开,脚步沉稳。

晚年时,钱钧把回忆录定名《我在山东十八年》。有人问他为何多“二年”,他眯眼笑:“师兄写十六,我就写十八,让他知道我比他多混两年!”玩笑背后,是一份不肯退场的倔强。两位少林俗家弟子,从嵩山脚下一路闯到共和国将星云集的旗阵前,命运编织得紧,也散得开,最后都化进记忆与青史。至于那句“这老头子,心还是热的”,如今读来仍带着火气,像嵩山寺庙黄墙上午后的阳光,猛烈却让人踏实。
迎客松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